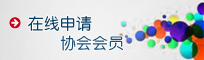当前中国经济的四大突出风险
时间:2015-07-13 09:54:00来源:未知 点击:0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部门、地方政府等部门资产负债率均低于国际警戒标准,总体风险可控。但与此同时,也要高度重视面临的苗头性和潜在性风险。
风险之一:财政收入大幅下滑是首要风险
2015年中国经济将要面对的首要风险是财政风险。这一点尚未被市场充分认识。具体来看,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和全国政府总收入的35%和23%,但土地招拍挂交易额在2014年下降了37%,伴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滑。地方政府收入的可能会低于2014年的2%,更远低于2009至2013年的平均值24%,这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首次下降。全国政府收入总额可能会在2015年增长1%,这也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德银通过对全国200多个地级市数据的分析,发现土地出让金占当地财政收入越高的地方,银行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在2008至2013年间上升的幅度也越大。这种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叠加意味着一些区域性的问题可能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地方融资平台受限的情况下,若当前的财政收入状况持续下去,那些高负债的省市地区偿债率将会进一步显著提升。
风险之二:非金融部门高杠杆风险突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05至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杠杆率由139.3%升至176.3%,近两年又继续升至约210%,上升了60多个百分点。根据标普数据,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共有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截至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将为1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7万亿美元。
过去5年,中国经常账盈余已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峰值的10%降至2013年的2.1%和2014年的2.0%。今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出现约800亿美元逆差,创历史新高且大幅超出去年四季度约300亿美元的水平。企业部门的自身造血功能开始下滑,为了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企业部门被迫采取加杠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兴经济体普遍出现经常项目账户恶化赤字和制造业部门杠杆率自2008年开始加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资本利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 1996-2012年期间,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3.9左右,与处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的ICOR数值明显偏高。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资金周转大幅度放缓增加了融资需求,但现金流创造能力却大幅度下降,这势必带来投资效益的下滑和实体部门偿债能力的下降。
风险之三:贬值预期和过快资本开放压力并存
跨境资本流动对一国金融稳定的核心观察变量,管控短期资本流动风险仍极为关键。过去两年内(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由115.2上升至130.4,升值幅度超过13%。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大致由国际收支差额决定,如果国际储备存量上升,则外汇市场上本币供不应求,本币存在升值压力,反之,则意味着本币供过于求,本币存在贬值压力。中国国际收支表上的国际储备变动额在2012年第四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连续7个季度为负,尽管该指标在2014年下半年为正,但在2015年第一季度再度减少802亿美元。这意味着当前市场上存在本币贬值压力。此外,从外汇占款增量来看,2015年1月至4月,外汇占款增量累计为-1891亿元人民币,表明金融机构在净出售外币,这同样表明居民与企业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
事实上,从2014年第二季度起,中国已经出现持续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以及短期资本净流出。2014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的短期资本净流出分别达到555亿美元、536亿美元与1016亿美元。这说明从2014年第四季度起,短期资本正在加速流出中国。更需关注的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的不断增加,反映出隐性资金外流增多。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用以保持收支平衡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自2010年以来已累计达到负3000亿美元以上,而2014年第三季度则创下了负630亿美元的纪录。这种资金外流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这类资金外流很难用监管手段加以控制。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利于中国金融稳定,毕竟在宏观经济基本面较为脆弱、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流出不利于放松金融条件、也不利于去杠杆,降低融资成本。中国目前处于降息周期,年底美联储加息概率加大,将进一步扩大国内外利差,对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造成较大冲击。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仍可以保留一定的资本项目管制,包括在反洗钱、反恐、外债和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等领域的宏观审慎管理和应急措施等,并做好系统性风险的应对预案。
风险之四:巨额场外配资折射金融监管漏洞
在中国股市场内场外融资的总体规模预计在3.3万亿元左右,悲观情况下可能达到3.5亿—3.7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资金1.6万亿元左右,约占股市配资的一半。报告还称,在1.6万亿元银行理财融资资金中,场内融资约10000亿元,其中两融融资8000亿元,收益互换2000亿元;场外融资约6000亿元。另外,股权质押项目吸收的银行理财资金约5000亿元,但未被计入场外配资。
就本质而言,当前场外配资公司+Homs系统+信托/民间P2P账户,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联网券商结构,配资公司在给投资者分配完分仓交易账户后,能通过信托配资/民间融资,直接让客户在自己账户上做高杠杆融资业务。
股市救市新政可能导致另类配资潮涌。据了解,目前大多数银行为上市公司提供质押融资业务提供的杠杆比率为1∶1,稍激进的商业银行最高能放到1∶1.5,甚至有些城商行将杠杆放到了1∶2,已经远远高过了融资融券的杠杆率,可能产生新的配资风险。
以上四大风险,内外联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决策层必须以有效化解并防范风险为首要前提,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风险预案和政策储备。
上一篇:中国连续19年成受反倾销调查最多国家
下一篇:世界贸易呈现结构性停滞